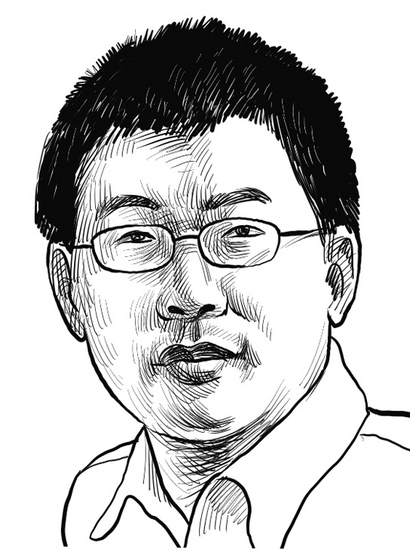
沈逸
复旦大学
国际政治系博士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网络逐渐深入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领域,形成了四个相对独立的业务范围:
第一是主要由国家安全局负责的对外信号情报搜集,主攻全球范围的非人力情报收集,主要配合依据《五国情报交换协定》所建立的“梯队系统”,监控美国境外的通讯活动;
第二是主要由联邦调查局和通信署等部门负责的内部信息安全保障和国内信息监控,目标是防御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的攻击;
第三则是主要由国务院,特别是国务院新闻署等机构负责的信息塑造与公共外交,借助对全球范围信息流动的控制(冷战时期主要是短波广播),以及在信息时代与各类新媒体配合的新型“数字外交”;
第四则是主要由美国国防部牵头,研究如何确保由信息技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惠及美国的军队。
上述分工合作,军-民领域和国内-国外事务分门别类处理的情况基本上一直持续到2001年9月11日,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多部门独立管理的多头模式逐渐无法适应信息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需求,美国逐渐开始了整合各功能部门的工作:首先是成立国土安全部,统管美国国内所有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防御工作;其次是在公共外交的旗帜下,强化突出美国国务院利用信息技术推进新外交的能力;第三是在国防部系统内部,通过任命国安局局长出任网络司令部司令的方式,整合军队系统内部应对信息战的能力。截至2010年10月20日,美国国土安全部与国防部发表联合备忘录,公开宣称将在人员、技术、设备等领域进行跨部门协作,以强化对美国国家信息安全的防御。
经过上述整合,负责实施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部分从最初四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划分,演变成了两个紧密联系与互动的纵向体系:
第一个体系以国务院为主要负责部门,任务侧重于“内容提供”,以追求对全球信息空间信息内容和流动方向的“塑造”与“控制”作为自身主要目标,这成为美国国家信息安全“软实力”的主要来源;
第二个体系表面上的牵头人是国防部,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旨在通过国家安全局在信号情报监控,与反监控方面庞大的技术资源,统合与信息基础设施防御和跨境预防性防御行动,为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提供“硬实力”的保障。
要实现这些目标,美国目前大致面临如下三个主要的制约因素:
第一,来自美国国内民众和民权团体的制约。冷战时期,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都有过监听美国国内民众通信而被抓包的丑闻,为此制定1978年《对外情报监听法》等法律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此次,不是直接宣布国土安全部和国家安全局的合作,而是借由国家安全局局长出任网络司令部司令,避免过度刺激民权团体在此问题上激烈反弹,是其中必然的考虑之一。不过从最近“维基解密”披露材料时的一些做法来看,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些主流媒体倒是似乎已被驯服的差不多了。
第二,因损害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价值中立与政治中立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收益,可能抵消美国政府塑造舆论空间的努力。冷战结束之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全球范围的高速扩散,政治中立与价值中立,或者至少说形式上的政治中立与价值中立,是其短期快速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美国开始不但实质性地强化对互联网信息内容塑造与流动控制,而且还公开表明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全球互联网用户对特定信息以及信息来源基本的信任,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损害其价值中立和政治中立的结果,便可能是导致整个数字空间的可信度大幅度降低。
第三,其他主权国家强化数字国界建设的努力。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展,当今世界的主要行为体仍然是主权国家,2010年10月25日,英国《每日邮报》披露谷歌“街景车”不仅采集家庭无线网络的名称等信息,还采集在无线网中传输的电子邮件和密码,英国信息专员表示将立刻重启对谷歌公司的调查。身为美国最铁杆的盟国,英国都不愿意放任与国务院合作关系密切的谷歌公司来收集本国公民的相关信息,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不难预料。最终的结果是否一定有利于美国或许还很难预料,但互联网注定因此面临被诸多国界切割得支离破碎大概是很有可能的。
就目前态势来看,奥巴马政府推动整合和强化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势头不会停止,新一轮围绕全球信息空间的激烈竞争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可能无人能够安全地置身事外。
(责任编辑:)





